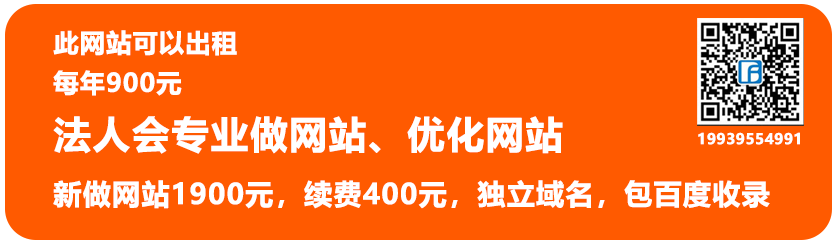“地球就是这么转的”——故事的魔性
“地球就是这么转的”——故事的魔性
发布日期:2017年03月03日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朋友圈
一
会讲故事的人,总能增强说服力。至于故事的真假虚实,并不重要。人们从虚构故事里接受告诫的冲动,从来不亚于真人真事;故事失真或虚构,不会降低我们寻求寓意或教诲的热情。
谁会介意 皇帝的新衣 是否实有其事呢?丹麦作家安徒生借助题材的童话属性,已经预先声明故事纯属虚构了,但人们倘想对专制君主的独裁本质发表点看法,仍会拿来举证,态度之严肃不苟,好像正在援引《论语》或某个科学实验报告。艾萨克 阿西莫夫统计过格林兄弟写的200个童话,他似乎认为统计结果具有相当的社会学价值,遂提醒我们: 男女人物的粗略统计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对比。故事中有16个邪恶的母亲或继母,只有3个邪恶的父亲和继父;有23个坏女巫,只有3个坏男巫;有13个年轻女子杀死或危害他们的爱人,只有一个男人伤害自己的新娘。 胡适喜欢收集 世界各国文字的怕老婆的故事 ,虽然此类故事多为民间戏言,注重 小心求证 的胡博士仍然得出如下 大胆 结论:
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 当时俄国是我们的同盟国,所以没有提起它,而意大利倒有很多的怕老婆故事,我预料意大利会跳出轴心国的,不到四个月,意大利真的跳出来了。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
古代肯定不是 自由民主的国家 ,而 河东狮吼 的故事并不罕见;诗人约翰 弥尔顿曾嘲笑论敌撒尔美夏斯 惧内 ,而那位法国文人当时正在舍命捍卫英国流亡国王的独裁主张 他付出了被弥尔顿活活骂死的代价。这构成对胡适结论的反驳吗?事实是,只要愿意找,每个故事都不难找出一打寓意,就像墙头草,常常你愿意它说明什么,它就能说明什么。试以 邪恶的继母 为例,它可能验证了俗语所谓 最毒妇人心 ,也可能如约翰逊博士所言,表明过去的作者都是男性因而乐意向女性泼脏水,而古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的解释,也可能更接近实情,他写道:
凡庸之性,后夫多宠前夫之孤,后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妇人怀嫉妒之情,丈夫有沉惑之癖,亦事势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与我子争家,提携鞠养,积习生爱,故宠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学婚嫁,莫不为防焉,故虐之。
你也许具有佛一般的慧眼,但是如果你不会讲故事,你的思想将像白垩一样枯燥无味。 (罗伯特 麦基语)说到故事的魔性,美国律政剧《波士顿法律》中的一个场景,有过极为刻薄的揭示:
年轻律师莎拉受困于一桩偷窃案的辩护,她向大律师阿兰 肖请教。肖律师未及听完案情陈述,就口气满满地提出了建议: 给陪审团讲个故事吧。 他告诉莎拉,不要担心故事是否牵强,只要最终将故事与案子强行联系,陪审团就会被说服,并眼泪汪汪地答应放人。 一个好故事也许就是一次机会, 肖律师补充道, 地球就是这么转的!
将信将疑中,莎拉作结案陈词时对陪审团讲起了故事:有一天我在厨房里做饭,看到自家的拉布拉多犬叼来邻居的兔子。兔子看上去是被咬死的,我担心邻居告状,赶紧把兔子洗干净,趁着夜色偷偷放回邻居家的兔笼。第二天,我听到邻居在外面对着苍天吼叫: 奇了怪了,我家兔子三天前就死了,我把它埋在树林里,居然有个促狭鬼把它又放回笼子,谁干的? 莎拉的结论是:不要轻信你的直觉,生活可能更离奇。她提醒陪审团,尽管本案被告的偷窃行为就像自家的狗咬死兔子一样不容置疑,真相仍可能在另一边,被告仍可能是无辜的。 静心一想,这个故事中的说教不是适用于一切法庭辩护吗?但见鬼的是,陪审团被说服了,他们作出了有利被告的判决。果然, 地球就是这么转的!
故事多半是编出来的,就是说,我敢肯定它并非来自编剧的生活积累。在美国文化里, 兔子 原是关于律师的著名典故,《波士顿法律》主角之一丹尼 克瑞的口头禅就是 在法庭上变出一只兔子来 ,而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辩护律师之一爱德华 本尼特 威廉姆斯,曾得到这样的评价: 他在法庭上应付自如,就像魔术师耍魔术时从帽子里取出兔子一样轻松自如。 他本人对此作的补充是: 如果你希望能够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拿出兔子那样在法庭上应付自如,那么,在进入法庭前,你就必须准备好50只兔子、50顶帽子。 我们也可理解为 准备好50个故事 。
美剧《大西洋帝国》的开头,也有一个类似桥段。具有奸雄品质的男主角伊诺克 汤普森,在一个圣诞夜的教堂里,向满脸虔诚的芝加哥大妈谈论政府实施禁酒令的必要性。他提到自己酗酒而早逝的父亲,是迫使自己家庭早早陷入贫困的直接原因。他提到自己少年时就被迫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艰辛备尝。当他讲到自己因捡不到土豆而不得不在 绝望中拿起扫帚柄,捕杀船舱中的三只老鼠,充作全家的晚餐 时,演讲在一片女性的唏嘘感叹声中达到了高潮。
走出教堂后,那位明显知道他早年经历的司机试图提醒他记忆有误,即根本不存在吃老鼠的事,他们当时实际上是吃了一顿狗肉。于是,借着昏黄的灯光,芝加哥奸雄向自己的心腹小老弟亮出了真实观点:
政界第一原则,孩子,别让真相毁了好故事。
故事在真相之上。只要故事产生了效力,真相即在其中。换句话说,对于 事实胜于雄辩 中的那个 事实 ,不宜拘泥理解为真实发生的事。能够打动人、感染人的故事,就会自动升格为 事实 ,并战胜他人的 雄辩 。 事实 的核心不是 真实 ,而是令人信以为真。人们认可了故事的寓意,真实与否就不再重要了,而各种启示会源源而来。
鉴于真相通常被认为只有一个,冒充的事实一旦成功上位,真的故事就会被踢下神坛,委弃在某个无人问津的语言陋巷里。 真理和谬误有着同样的传播方式 (卡斯 桑斯坦语),每一种谬误都会宣称自己为真,因此,认为真实在与虚假的斗争过程中总能获胜,多半是一种心理自欺。实际上,当奸雄伊诺克 汤普森虚构自己的故事时,他品尝到了莎士比亚笔下奥瑟罗向苔丝迪蒙娜讲述自己身世时的那种奇异效果,奥瑟罗当时是这样说的: 当我讲到我在少年时代所遭逢的不幸打击的时候,她忍不住掉下泪来。我的故事讲完以后,她用无数的叹息酬劳我。 奥瑟罗的身世描述里还包括 肩下生头的化外异民 ,那不应该是真实的见闻,但苔丝迪蒙娜被深深打动并决定爱上他,则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在文学作品里品尝到的故事,有着最高的精神芬芳;在说教世界听到的故事,则可能带有令人迷醉的剧毒。说者在 狗肉 与 老鼠肉 之间随意切换,足令听者晕眩,从而接受他的任意指引。
故事之于人类,是一种堪与 七情六欲 匹敌的本能式力量,对此,英国作家毛姆有过精准的评价,他说, 倾听故事的愿望就像拥有财产的愿望一样,在人类的内心可谓根深蒂固。 童话永远是孩子最好的精神伴侣,而我们擅长做梦的事实更具说服力:再不会讲故事的人也能做梦,梦中人具有梦醒时所远远不具备的能力。在梦中,我们既是梦境的创造者,又是感受者和旁观者,我们即兴创造,即时感受,进入一种超验的时空。梦中五分钟,梦外一小时,这大概就是潜意识与意识的差距。电影《盗梦空间》里的科学家认为,梦中人的大脑思维速度比清醒时快20倍。我不知依据何在,但似乎大体符合我们的经验,且姑妄信之。总之,眼睛一闭,秒变超人,我们即使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个故事,也有能力在每个夜晚进入出其不意的故事当中。成为故事人,就是我们的休息方式。
故事源自生活,但生活中的人很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故事中,所有那些日后被论定为悲剧人物的家伙,当他们活着时,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正成为一部悲剧的主角。喜剧人物亦然。这表明,只有被人说出的生活,才是故事;生活只有被重新打断、组装,被强行掐头去尾并重新安排一个结尾,才具有故事性。而一旦生活得到故事家的重新制作,意义随之产生。我们对自己做过的梦,都会热切地揣想其意义,愿意将崇拜的眼光,投向那些声称可以阐释梦境的人,这也是当年弗洛伊德等人得以凭借精神分析术大获成功的原因:他们的成功奠基于人类最深沉的心理需求之上。
故事一经说出,就有了法力,而未经说出的生活,只配沉沦。罗伯特 麦基说得好:
简言之,一个讲好了的故事能够给你提供你在生活中不可能得到的那样东西:意味深长的情感体验。在生活中,体验需通过事后的反思变得有意义;而在艺术里,体验在其发生的那一瞬间马上就会具有意义。
二
古斯塔夫 勒庞对历史书抱有强烈的偏见,他认定 历史全是一派胡言 ,断言 只能把史学著作当做纯粹想像的产物。它们是对被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掷光阴 。说勒庞偏激是很容易的,但否定他的睿智成分,又失之简单。
海量事实告诉我们,后人听到的历史故事,未可尽信,有些甚至可以肯定是荒唐和错误的。我们相信某些故事存在过,或出无奈,因为我们缺乏别种渠道可资验证,也缺乏别种史实作为代偿。如果否认这些历史故事的存在,我们毫无所得,还将面临文化资产的净流失。比如,虽然孔子问道于老子的故事写得并不扎实, 鸿门宴 的故事似乎又过于绘声绘色了,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否认它们都不如接受它们来得实惠和有利。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 朱贝博士说得坦率: 在耶路撒冷,不要问我真相的历史,若拿走虚构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无所有了。 别的文明也大抵如此,唯程度各有不同。
我们会非常愉快地接受荷马或施耐庵的艺术欺骗,但被历史学家欺骗,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本该是我们最可信赖的真相守护者。我们通常不会先行假定历史学家说谎,除非凑巧遇到了证据。比如,下面这个由余英时先生发现的证据,就让人极度震惊。
余先生获邀先行审读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重新编校的洋洋四百万字的《胡适日记全集》,由于该版 增加了一些以前未收的新资料 ,所以被认为 最完整 。余先生腹笥雄厚,见闻广博,阅读过程中会不时联想到他人著述,以供核实或释疑。他之前从历史学家罗尔纲《关于胡适的点滴》一文中读到胡适于1930年11月28日那天 全家从上海迁北平 时的奇特遭遇,据罗尔纲描述,那天的车站气氛怪异, 人们认为(国民党)特务会在车站狙击胡适 :
这天上午约八时,我随胡适全家乘出租汽车从极司非尔路到了上海北车站。我跟胡适步入车站,走上月台。满以为胡适广交游,今天一定有不少亲朋到车站来送行。别的且不说,胡适夫妇与上海金融界巨子徐新六夫妇最相好,连两家孩子也相好。 可是这些人,今天连影子都不见。为什么亲朋满上海的胡适今天却一个人都不来送行呢?我心里嘀咕着。 我忽然听到对面那边月台上有人大叫胡校长。我和胡适都掉转头来,只见一个公学同学,边跑来边说: 学生会派我来送行,请胡校长等一等,要照个相。 原来那位同学在车厢对面那边月台上远远地站着,等候胡适到来,见胡适要上车时才喊叫。他跑近了,匆匆把照相机对着胡适拍了照,就立刻飞快地跑出了月台。这时我才意识到今天究竟是怎么一个场合。
余英时找到胡适那天的日记,想看看胡适是怎么写的:
今早七点起床,八点全家出发,九点后开车。到车站来送别者,有梦旦、拔可、小芳、孟邹、原放、乃刚、新六夫妇、孟录、洪开 等几十人。
饶是余英时见多识广,他也被两种叙述间的巨大出入,弄得傻了眼。我相信,余先生写下这段话时,一定抱着极大的克制:
我不愿意去猜测他 (罗尔纲)的动机,但是我敢断言,这是他想以浓墨刻画出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所以才虚构出这样一篇绘声绘影的绝妙文字来。我不能不佩服他想象力之丰富,但是如果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不幸遗失,罗先生的虚构便将被后人当成实录了。
从故事角度说,这个例子并不精彩,它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这是由一个按说最知晓秉笔直书价值的学者,在一个最不值得撒谎的地方,撒下的一个荒唐谎言。罗尔纲曾是胡适 最亲近的一个后期学生 ,著有《师门辱教记》,胡适曾给予他极高评价,认为他具有 狷介的品行, 在行为上能够 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 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 ,胡适赞美罗尔纲 谨慎勤敏 ,并热烈地预言道: 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多奇怪,就是这样一位史学人才,竟从容淡定地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放胆撒谎,听上去就像亿万富翁在超市里偷走一支牙膏一样可笑。
古罗马哲人塞涅卡曾经感叹道: 甚至在说谎的一切原因都去掉了的情况下,我们还将发现习惯就是说谎的一个原因。 维特根斯坦也说过: 一个人懂得太多就会发现,要不撒谎很难。 我猜,他们有此感慨,当是因为见到了各种罗尔纲。
再来看看历史书里的名人死亡。弗吉尼亚 伍尔芙曾在《读不懂希腊文》一文里提到若干古希腊名人的死法: 欧里庇得斯是被狗吃掉的;埃斯库罗斯是被石头砸死的;萨福跳崖而死。关于他们我们只知道这些,仅此而已。 但她随即补充道: 但是也许这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全部真相。 这个补充很有必要,因为关于埃斯库罗斯之死,还有更加神奇的说法,一说他是被乌龟砸死的,并且, 那只乌龟是从埃斯库罗斯头上飞过的一只老鹰的爪子里落下来的。那只老鹰把他的光头看作了一块石头。 哪个才是事实呢?没人知道,这些说法都来自古代史学家,我们不清楚哪个更可信,你愿意相信哪个,你觉得哪个更有趣,就不妨采纳哪个。
我国也有类似难局。借助小说和戏剧,国人都知道诸葛亮斩马谡的故事,但马谡到底怎么死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没有说清楚。关于马谡的死因,陈寿其实提供了三种说法,黎东方在《细说三国》中写道:
(一)诸葛亮诛了马谡,戮了马谡,也就是斩了马谡。(二)马谡于关在牢里以后,死在牢里。(三)马谡畏罪逃亡,丞相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免职,斥令回成都。陈寿把第一种说法,写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与《王平传》;把第二种说法,写在《马良传》;把第三种说法,写在《向朗传》。
今人采纳 斩马谡 之说,只是因为这个故事更有嚼头,可以证明诸葛亮执法严明,军令如山。如果采纳马谡逃走说,一个好故事就失去了。那几乎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损失。
美国著名刑辩律师李 贝利,对于案情唯有经过充分质证方可采信这一点,有着更深的认识。他在法庭上见识多多,对证人的撒谎也有更多的思考。他认为,同一事实出现多种说法,是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在描述某个事件时,都会把自己 对当时情况的推论错误地当成当时看到的情况 ,他认定某人是凶手,就会将与之合拍的情节视为实际发生,并在想象过程中将其固化。这也许可以解释 罗生门 现象,但不能解释罗尔纲,也不能解释王小波。在《思想和害臊》和《沉默的大多数》两文里,王小波叙述过同一件事,即某知青由于没有付够钱而遭村民大骂。奇怪的是,他前文刚说自己挨骂,后文突向读者保证,挨骂者 决不是我 。假如王小波对故事怀有既定推论,他就该固守一个说法。我相信王小波并无恶意,但这又说明,即使全无恶意,你也可能在讲故事时忽左忽右。故事总是不太靠谱,几乎没有一个故事,曾被不同的目击者说得一模一样,但故事的力量恒在。
曹操曾被一篇犀利的檄文骂得狗血喷头,时过境迁后人们发现,一些编造的故事对他打击更大,如说他出于疑心杀死款待自己的老好人吕伯奢一家,还留下一句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的恶语。有学者考察了当年曹操的逃亡路线,令人信服地证明此事不可信。可惜用处不大,人们并不愿为了一份诚实而牺牲一个好故事。类似例子今天也有,在2008年,为了打击竞选对手,有人虚构阿拉斯加州长莎拉 佩琳的种种蠢行,如说她认为非洲不是一个大洲,而是一个国家。也许正因为这些虚构过于离奇,当时 很多美国人都相信了 。
我们热爱会说故事的人,有时也得警惕他:取决于他们仅仅想说个故事,还是借机宣布一个主张、宣判一个罪人。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试图驱逐的诗人,原是以荷马为代表的故事家。柏拉图当然也热爱荷马。沃尔特 李普曼告诫我们: 只要记住几乎每一个政党都会深信不疑自己为对手所描绘的画像 它认为那就是真相,但那并不是真相,而是它想象中的真相 我们就会完全理解战争与政治的暴烈。
故事世界里有白天,也有黑夜,我们被迫在真假莫辨的世界里沉浮流转,同时假定这些故事意味深长,发人深省。 地球就是这么转的!








![郑州黄河食品城[官网] - 郑州食品城 郑州黄河食品城[官网] - 郑州食品城](http://cdn6.bao-fang.com/0013/images/wenhua_gg.jpg)